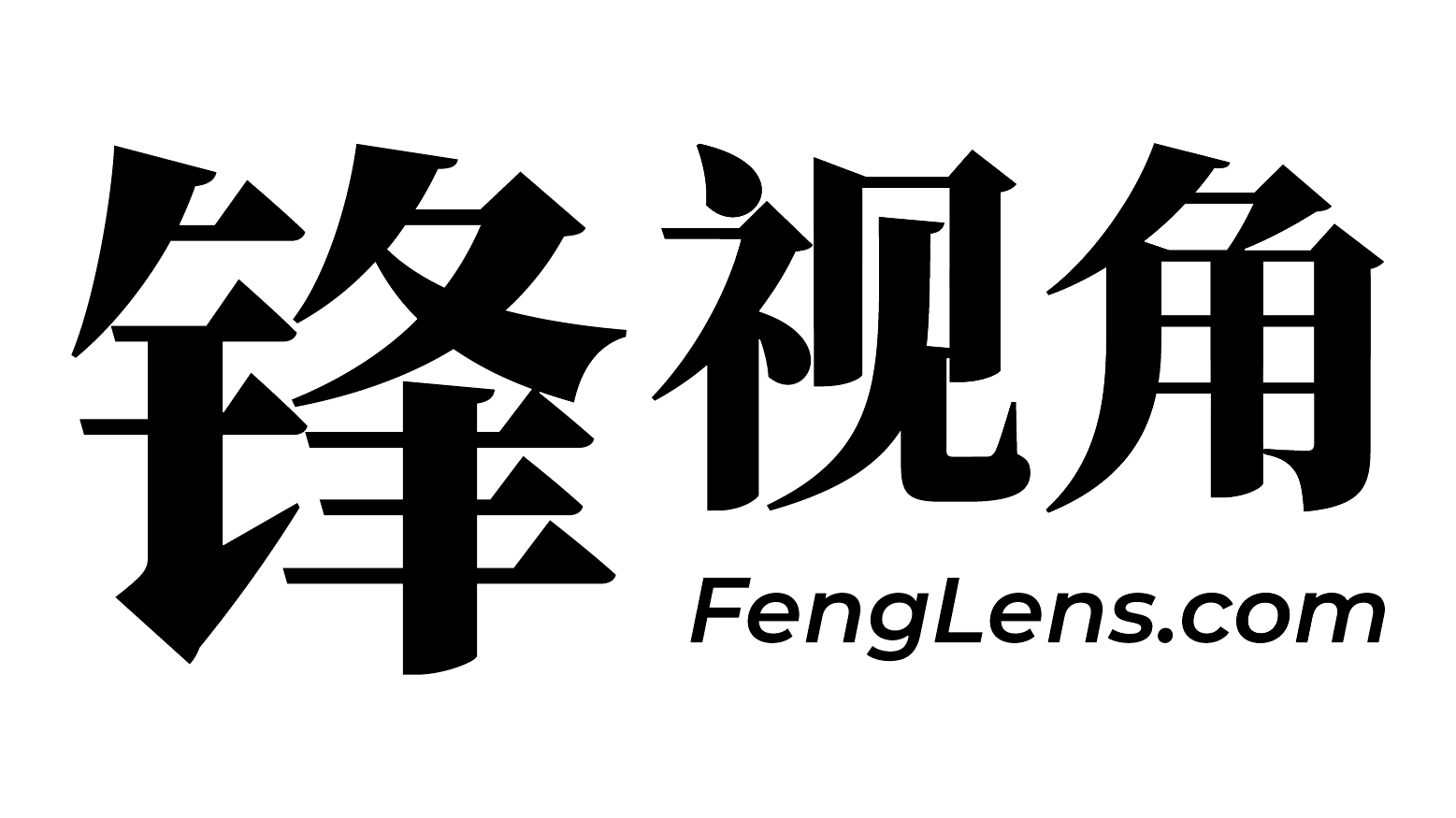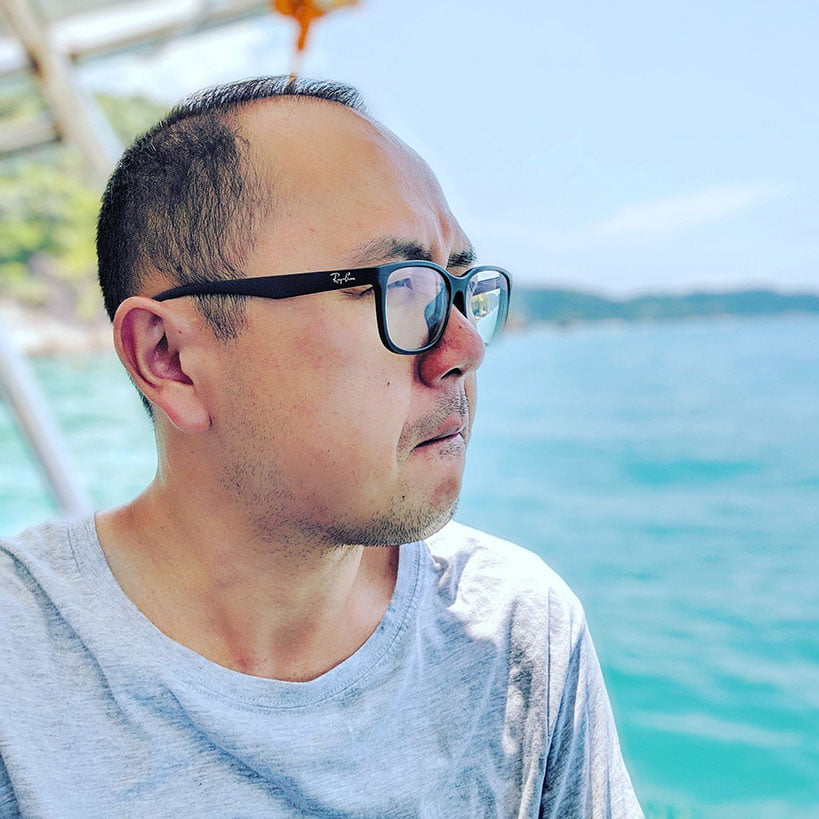文:陈君武
无可否认,在马来西亚政坛,首相安华是一位拥有非凡政治韧力的领导者。他用了二十多年才等到首相之位。这一个位置本应是他兑现“改革派”理想的历史时刻,但现实却显示,他在权力的巅峰,却也立于政治的钢索之上。
安华并非以单一政党的胜利执政,而是通过“团结政府”的结构执政成为首相。这个政府由原本敌对、互不信任、甚至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对立的政党组成,包括巫统、砂拉越政党联盟(GPS)、沙巴政党联盟、诚信党、公正党以及行动党。这种看似团结的组合,但实质是一种脆弱的妥协,是个没有单一强势主体的“共享政权”。安华虽然贵为首相,却必须不断在不同势力之间平衡。只要任何一个关键集团撤回支持,政府就可能垮台。这种执政结构赋予他权力,却也削弱了他的主导权。

马来选票的流失
对安华来说,最根本的困境来自马来选民基础的流失。在2022年大选中,他领导的公正党并未赢得多数马来票,反而是伊党与国盟成功动员了乡区保守群体。伊党也通过宗教情绪、身份焦虑与种族叙事,将安华塑造成“受行动党影响”以及“偏向华人”的领导者。指控他会削弱马来特权。虽然这些指控缺乏事实基础,但在社交媒体及宗教演讲上却非常具有说服力。
当政府推动任何形式的财政改革,尤其触及补贴制度时,这种不信任迅速被放大。柴油补贴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负担,并打击走私与黑市,将柴油补贴从全国性补贴改为针对特定行业和车辆类型的“定向补贴”。这一政策从宏观看来具有理财合理性,也符合国际机构对马来西亚财政改革的期待。然而在马来乡区,这项政策被普遍解读为“政府削减马来人的福利”。许多依赖柴油作为生产与交通成本的基层群体感到不安,甚至部分巫统地方领袖也公开表达不满。这场风波不仅没有为安华加分,反而进一步加深了马来选民对他的疑虑,让他陷入“改革必须做,但做了就失分”的结构性困局。
华社的现实主义与失望
同时,华社对安华的情感极其复杂。华人社会曾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,也坚定的相信安华会推动制度改革,反贪、恢复司法独立、改革教育与经济结构。然而过去两年的执政期间,在现实政治的掣肘下,安华在许多改革领域陷入停滞。柴油补贴调整引发民众普遍焦虑后,政府为了安抚情绪放缓其他补贴改革的步伐,这令支持改革的华社认为政府缺乏决断力,也担心改革进程再度被搁置。许多华人选民虽仍支持安华,但这种支持越来越倾向务实。不是因为相信改革必然成功,而是因为惧怕保守势力,如“绿潮”卷土重来,可能带来的更大不确定性。因此,在华社间,掀起了下一届“宁愿在家睡觉,也不愿出来投票”的声音。

宗教与身份政治的高压环境
在权力结构的另一端,伊党和国盟的政治攻势持续不歇。他们不断通过州政府平台巩固基层,推动伊斯兰法案的象征性立场,以塑造“真正保护马来穆斯林利益”的形象。柴油补贴风波成为他们最有效的政治武器之一,他们将其描绘为“政府偏向华人企业利益、忽视马来基层生计”的证据。这种叙事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,尤其以马来群众为主的TikTok,以及在宗教演讲中被反复引用,使安华的政府被迫进入防守状态。他既不能否定宗教地位,也不能允许国家被拖入神权化的道路,必须维持一个世俗宪政框架,同时说服马来群众相信改革不会威胁他们的身份。
经济作为突破口
经济是安华希望突围的最大筹码。他提出“昌明经济”,推行财政重组,吸引外资,加速数字与绿色转型。马来西亚的国家信用评级保持稳定,外资回流迹象明显,制造业增长回暖,这些指标对国际市场具有吸引力。然而,这些宏观数据尚未转化为普通人民可感知的日常改善。柴油补贴风波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落差,许多人认为政府在讲经济成长的宏观叙事,却未能解决他们手中的油价、生活成本与购房问题。生活压力持续高涨,中小企业面对消费低迷,马来乡区依旧依赖补贴维生。安华必须在财政纪律与民生补贴之间找到平衡,这意味着他不可能推动任何激进改革,只能小步试探。
国际舞台的声望
在外交的舞台上,安华展现了强势姿态,特别是在巴勒斯坦议题、区域经济秩序与中美竞争平衡上,他成功塑造“道德型领袖”的国际形象。这种外交声望对内政有所帮助,因为强化了他作为“穆斯林世界代表”的地位,抵消伊党的宗教品牌。但外交影响能不能直接转化为选票,是否能够在马来选民心中重建信任,他仍需打造一套新的国家叙事。不是旧式的“马来至上”,也不是单纯的“多元共享”,而是能够说服马来群众相信:改革是为了他们的未来,而非威胁他们的地位。

安华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役?
安华的政治处境是一种矛盾状态:他手握政权,却在权力分配中处处受限;他是改革设计师,却无法主导改革节奏;他拥有国际声望,却依然需要更努力的说服本国多数民族接受他的领导。柴油补贴风波显示了,任何改革只要触碰马来基层的心理防线,就可能被政治对手转化为攻势武器。在这种局面下,安华仍可能稳住政权,但要真正翻转政治格局,他需要的不只是政策,更是一场深层的社会心理重塑。或许,来临的全国大选将是他政治生涯最后、也是最艰难的一役。
相关影片